
10岁的马修·莫洛伊(Matthew Molloy)博士还是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一名学生时,他知道自己必须参加某种形式的“工作见习”(job shadowing),跟着一位医生一天或更长时间,提出问题,观察医生与病人的互动。
“我认为这些见习经历是如此多变,”莫洛伊说,她现在是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的儿科住院医生。“有些人可以有很棒的影子体验,但我几乎觉得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打勾。”
大多数做“影子医生”的人无法深入九博体育研究医生的想法,只能接触到一种药物。此外,如果医生一天很忙,可能很难问问题或得到建议。到2020年,由于COVID-19大流行,这种做法戛然而止。
然而,大流行创造的参数引发了圣母大学大四学生泰勒·丹恩、利亚·古德克斯和亚历克斯·尼斯贝特的一个想法。这三个朋友一起在圣母大学职业预科协会(Notre Dame Preprofessional Society)的领导九博体育(亚洲版)在线官网任职,该协会去年秋天通过Zoom与医生们举办了一个系列演讲。系列课程完成后,他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做得更多:创建一个完整的课程,让圣母院的校友医生可以与下一代联合医疗工作者分享他们的经验。



丹恩、古德克斯和尼斯贝特找到了本科九博体育研究助理院长兼职前九博体育研究顾问凯瑟琳•科尔伯格(Kathleen Kolberg),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在延长的寒假期间开设一门1学分的课程——几乎类似于虚拟的“工作见习”体验,同时还要阅读高级生物和医学物理读物。
丹恩说:“她说这个主意太棒了。从11月中旬开始,我们帮她写了一份课程建议和教学大纲,并申请了冬季学期的课程。”他开始通过大学的专业人士网络爱尔兰指南针联系不同的医生,看看谁愿意为课程贡献时间。
总共有九名医生参加了这门名为“医学生物医学案例九博体育研究”的课程,该课程于1月4日至26日在冬季课程中每周举行三个晚上。共有39名学生参加。
丹恩、古德克斯和尼斯贝特担任这门课的助教,这门课一部分是基于案例的,由医生们做报告,一部分是讨论。
丹恩说:“这与亲自跟随有很大不同,但在某些方面,我们能够从中获得更多。”“与物理影子相比,虚拟影子使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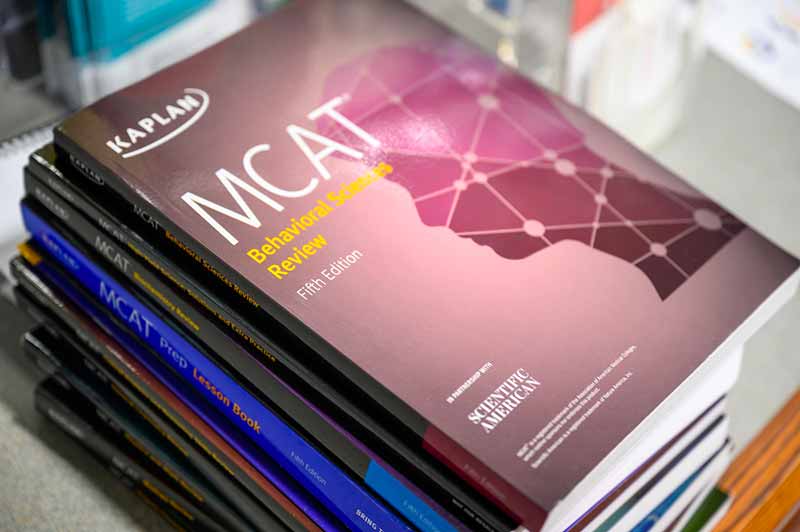
参加培训的医生在每节课前都会分享指导阅读或视频材料,这些材料为学生提供了医生计划讨论的病例的背景。演讲结束后,医生们开始了问答环节。
学生们让医生完全控制自己的课堂时间。“我们不想提出具体要求;医生才是专家,”古德克斯说。“他们会给我们发送与他们九博体育研究领域相关的多个主题,他们会问我们最感兴趣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会按照这个主题去做。”
卡莉·瓦格纳(Kari Wagner)博士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的新生儿科医生,她也把教书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并觉得这份工作很充实。对她来说,为圣母大学的学生准备一场关于新生儿黄疸的讨论是激发求知欲的另一种方式。
她说:“我真的很喜欢,教学生一些东西,让他们对这些材料感到兴奋,更加投入,这很有成就感。”“这是对亲身见习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有可能让学生接触到更广泛的医学和专业,因为大多数见习只能看到一个专业。”
宾夕法尼亚大学放射肿瘤学家蒂姆·凯格尔曼(Tim Kegelman)博士同意这一观点。他与学生们分享了接受肺癌诊断的过程,并强调了“他们以前可能没有接触过的专业”。他说:“这是一个小众疗法,但却是癌症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尔伯格说,对学生来说,最大的好处之一是有机会听到医生和其他专职医疗人员如何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这是她作为顾问与学生们分享的。Aaron Quarles博士在西北纪念医院的急诊科工作,在分享更多关于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之前,他介绍了一些他的背景信息。

他说:“让10到15个人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大声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必须有人站在那里指导,这就是我的角色。”“我试图为病人争取时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争取时间。这向学生们展示了成为一名医生的不同方式。”
他描述了成为一名医生的实际情况与人们想象中的医生有多么大的不同。他说,人们考虑的是声望、金钱或智力,但夸尔斯指出,医生的知识仍然有限,必须与他们的团队和病人合作来解决问题。
他还分享了无法尽可能多地帮助病人的挫折感。例如,如果有人有心理健康危机,而他不能立即为他们找到一个机构,他们就被“困”在急诊室里,没有隐私,所以这对病人解决他或她的危机没有帮助。
23岁的卡伦德里亚·“拉拉”·佩蒂想参加一个冬季课程。虽然她想在西班牙语国家做一名运动物理治疗师,但她也对产科医生/妇科医生或急诊室医生的潜在工作感兴趣。因此,佩蒂很高兴听到不同专业医生的来信。

“即使在他的工作中,他也会给人一种感觉,如果他代表什么,他就代表什么,在这段时间里,这是如此重要。——carlondrea“Lala”Petty, 23年
她最令人惊讶的收获之一是:她觉得自己与几位发言的医生有联系,尤其是夸尔斯。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在圣母大学创立了黑人学生协会,她现在是董事会成员。
她说:“我没有指望从这门课上得到认可,因为我是一名黑人女性。听到夸尔斯的演讲,以及他作为一名黑人男性的经历,真的很重要。”“即使在他的工作中,他也会给人一种感觉,如果他代表什么,他就代表什么,在这段时间里,这是如此重要。”

“就连移民到这里的委内瑞拉医生也谈到了如何很难跟随,所以我非常感谢利亚和其他助教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瓦伦蒂娜·埃斯皮诺萨22岁
对于22岁的瓦伦蒂娜·埃斯皮诺萨(Valentina Espinoza)来说,坚持某种东西很重要,她一直在决定是成为一名医生,还是进入公共卫生和公共政策领域。在听说了不同的专业和医生的生活方式后,她意识到对她的吸引力更大的是公共政策,在那里她可以影响变革。
然而,对于那些想成为医生的学生来说,在课堂上“影子”的机会对那些与医生没有联系的学生很有帮助,她说。
来自委内瑞拉的埃斯皮诺萨说:“对于许多第一代学生(那些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来说,新冠肺炎是因祸得福。”“就连移民到这里的委内瑞拉医生也谈到了如何很难跟随,所以我很感激利亚和其他助教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Lena Do ' 21很欣赏几位医生的讨论,他们不仅讨论了成为医生的过程,还讨论了他们个人职业生涯的演变。一位内科医生讨论了成为一名医生意味着什么——这是大多数人不会想到的:医生就是会犯错的人。他们不能结束所有的痛苦,即使他们想这样做。

“我开始明白,人生没有最终的目标,也没有事业的巅峰。从我进入医学院一直到退休,这都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职业。——莉娜·多
“我开始明白,人生没有最终的目标,也没有事业的巅峰,”杜说。“从我进入医学院一直到退休,这都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职业。”
健康科学咨询中心副院长兼主任詹姆斯·福斯特博士说,由于冠状病毒的广泛使用,在线学习成为了一件幸事。尽管许多人希望回到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但该课程的在线性质使来自全国各地的校友能够以一种以前无法做到的方式与学生建立联系。
福斯特神父对爱尔兰指南针指导数据库表示赞赏,并赞扬了医生们对班上学生的慷慨帮助。
福斯特神父说:“这有一个缺点,它不太像影子,在那里你可以闻到这个地方的气味和感觉,并观察团队的合作性质,包括与病人的联系——但这是有价值的,而不是我们以前使用的机会。”
“我花了很多时间微笑,”科尔伯格说,她帮助学生开发课程,然后看着医生做报告。“我很感谢校友们,因为他们如此慷慨地投入了时间。”
参加课程的学生和医生都同意,即使在COVID的威胁过去之后,课程也应该以某种形式继续进行。

佩蒂说,她会向其他考虑任何健康领域的学生推荐这门课程,“因为医疗保健系统中充满了许多相互联系的人,了解系统如何运作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也很有帮助。”
夸尔斯说,他希望自己在学生时代就能有这样的机会。
他说:“除了不是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见习之外,如果能和几位年轻医生在一个房间里交谈就好了。”“因为作为一名大三学生,你还要接受10年以上的学校教育和培训,和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人谈谈这个过程是很好的。”
儿科医院医生莫洛伊赞扬了科尔伯格和开发这门课程的学生,并补充说,这是圣母大学可以用来帮助学生进入医学院的另一个工具。
他说:“尽管圣母大学没有医学院,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学生和导师在申请医学院之前,如何让学生获得他们需要的经验,并帮助他们做出决策,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母大学在让学生被医学院录取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像这样的项目证明了他们的项目有多好。”


